来源:本网采编
发布时间:2021-05-25 11:06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赵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构成了国际经济体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2018年7月6日,美国打响“关税战”第一枪,中国随即采取反制措施。其后,双方进行了多轮交锋,两国之间筑起了极高的关税壁垒。不仅如此,美国还对华发动“技术战”,即中国部分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威胁实施出口管制。特朗普政府发起的空前烈度的对华贸易战构成了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持续了40年之久的美国对华经济接触战略的终结。
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迎合了美国国内部分势力的战略和利益诉求,但它也招致了中国同样剧烈的关税反制措施,进而造成了美国国内部分群体特别是对华出口产业的巨大利益损失,因此在美国国内产生了众多或明或暗的反对力量。2018年7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88:11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非约束性决议,寻求扩大国会在限制总统加征关税方面的作用。虽然这次投票没有给国会任何真正的权力来限制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但它反映出不少国会议员在“关税战”上与总统的分歧,而议员作为各自选区选民的集中代表,是美国社会不同群体立场和偏好的“传声筒”和“晴雨表”。这些反对力量成为特朗普在2019年急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重要推动力。
由于美国的产业呈现高度的地理集聚的特征,在中美贸易战中利益受到损失的产业最终会通过它们所在选区的政治代言人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准确理解中美贸易战中的产业地理政治,成为理解中美两国政府在经贸谈判中变换采取“进攻”与“妥协”策略的逻辑基础。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认为,以产业集中分布为特征的产业地理和以选区为中心的政治地理共同构成了美国国内社会利益和偏好向上传导的核心机制,也共同构成了左右美国联邦政府对华经贸决策的微观利益基础和动力机制。由于美国对华“关税战”的影响范围要远远大于对华“技术战”,本文的实证部分集中关注美国“关税战”的利益受损方,即美国的对华货物出口行业的产业地理政治,试图厘清中美“关税战”中美国国内的潜在反对力量,进而服务于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反制政策。
二、把地理因素“找回来”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关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讨论可谓浩如烟海。经济学者认为,一国不实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主要依据最优关税论、减少失业论、“幼稚产业保护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等几种理论论点。但任何国家层面的政策都事关政治过程,它不是中立的技术官僚简单基于经济逻辑所做出的,对于美国这样的选举制民主国家更是如此。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的:“单靠经济学这个工具做不到精确和充分。”因此,对美国贸易政策的解释需要政治学的介入。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过将政治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大大提升了对贸易政策的解释力。
(一)从体系层次到国家层次的回落
按照研究层次和单元的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的对外贸易政策研究首先可分为国际和国内两大视角。国际视角主要从体系层次的变量出发,如霸权稳定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分别从国际权力结构、国际市场条件和国际制度环境三个角度解释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行为。但是,体系层次的理论视角有其固有缺陷,它虽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国家行为的外部结构性环境,但却无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决策的微观逻辑,因为国家并不总是依据国际体系的结构来决定自身的行为。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以“强社会—弱国家”为特征的国家而言,其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制度安排的作用。因此国际视角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同一或相似的国际体系下美国有时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有时又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窠臼。不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都认为要加强对国家内部特征的研究,否则不能充分理解其对外经济政策。
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国内视角又包含两条具体路径:一条强调国内社会利益分化与政策竞争,另一条强调政治家与国内政治制度的作用。国内社会路径主要以公众或利益集团等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与游说行动来解释国家政策结果,早期解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主要依循这一路径,强调关税保护主要是利益集团政治施压的结果,美国学者埃尔默·沙特施耐德(Elmer E. Schattschneider)对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的研究是最早的经典案例。国内社会路径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制度在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因果地位”。与此对应,国内制度路径认为一国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并非总是被动地聚合和反映社会行为体的利益,政治家、官僚、政党、行政或立法机构等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以及它们赖以行动和实现目标的制度框架更加重要。因此,有学者尝试将上述两种路径加以融合:比如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借助政治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s of politics)来展现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并尝试说明偏好与制度的变动情况及其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基恩·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建立的“保护待售”模型通过将贸易政策看作利益集团与政府博弈均衡的结果,将二者不同的政策偏好结合考虑。
总体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下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体系层次到国家层次的回落,实际上是打开了“国家”这一黑箱,将国内社会和国内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框架。这对研究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至关重要,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最有能力超越国际体系的约束,其贸易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的结果。所以,有关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大多遵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内路径,聚焦于美国贸易决策机制中的总统和国会这两大主体及其权力消长和互动关系。鉴于国会在美国贸易决策机制中的关键作用,国内出现了许多关于美国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将过多注意放在国内制度上,而相对忽视了社会利益,也就无法说明美国贸易决策背后的微观利益驱动机制。
(二)产业地理与美国贸易政治
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直接关乎不同产业的利益,而政治人物主要依据选区利益进行决策,选民的选票是政治人物的“母乳”。因此,各种产业在不同选区的地理分布成为政治决策的关键因素,在产业地理基础上所形成的选区利益构成美国贸易政治重要的微观动力。
在国外有关文献中,关注到地理因素的首先要数美国学者温迪·席勒(Wendy J. Schiller),她于199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试图解释产业分布如何影响该产业的联盟策略。席勒认为地理因素是内嵌于“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这个更广阔的概念中的一个解释变量,并将这种联系定义为产业经济地理(即财富生产所在的地理位置)与它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产业经济地理主要指产业从事经济活动所在的地理位置(location)、地理范围(geographical reach)和地理集中度(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席勒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出口型产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横跨多州的产业在众议院权力更强,而集中在较小或中等人口规模州的产业在参议院的权势更强,所以它们一般寻求与自己具有不同分布特征的产业进行联盟,以弥补自己在国会另一院的劣势,同时保证联盟规模尽可能地小以降低成本。另一篇较为重要的文献来自马克·布希(Marc L. Busch)和埃里克·莱因哈特(Eric Reinhardt),他们关注的是产业分布如何影响贸易政策结果,他们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美国进口竞争型产业的分布特点与争取贸易保护的关系,对于大多数较小规模的产业而言,在选区分布上越分散越容易争取到保护。而产业规模的增加会削弱低地理集中度的政治优势,对于少数规模极大的产业而言,较高的地理集中度反而会更有利。
中国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产业地理因素与贸易政策制定的关联。其中,孙哲和刘建华最早援引席勒的解释而提出“产业地理政治”的中文概念:“就美国的情况而言,美国的‘政治制度结构’就是美国府会间分权制衡以及国会参众两院间在决策权力方面的分配及互动机制,所以美国产业地理政治主要指美国的产业经济地理与国会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他们还阐述了美国产业地理分布范围和集中度与其在国会政治影响大小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运用实例从产业结盟游说的角度考察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国会因素。孙哲和李巍不仅揭示了美国国会对华经贸决策的产业地理基础,并对如何利用美国产业地理政治规律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提出了六条建议。此后,刘建华又从贸易与产业的互动、产业与国会的互动、国会与行政部门及独立机构的互动这三重递进层次,就产业地理对美国对华贸易决策的影响机制做了理论阐述。王颖则简要描述了美国对华出口产业的地理分布,并利用国会议员的投票数据和贸易态度数据,总结了五种产业分布类型及对应产业的对华贸易态度。
总体而言,目前将产业地理与美国贸易政治关联起来的研究还不太充分。由于美国的产业地理格局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再次暴露出美国产业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不少研究认为特朗普发起此轮贸易战旨在保护五大湖区域衰落的传统制造业的利益,而该地区汇集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主要“摇摆州”。本文将在充分阐释产业地理政治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考察美国四大主要产业的地理分布特征,着重分析美国对华货物出口行业在中美“关税战”中的产业地理政治形态,尝试为调动美国国内的反关税战力量、改善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一个路线图。
三、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理论逻辑
贸易政策会在美国内部不同产业间产生利益分配效应,日益凸显的产业集聚现象则进一步导致这种贸易收入分配在地区间的分化;同时由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又主要体现为以地理为基础的代议制,选举制度和选举过程将不同地域的利益和价值传达到联邦层面,并通过联邦政府的政策加以实现。因此,以产业集中分布为核心的产业地理便成为塑造美国贸易决策的关键因素,在产业地理基础上所形成的三种类型的选区利益构成美国贸易政治重要的微观动力。这三种类型的选区分别是总统的全国选区(实际上是对总统大选具有决定意义的若干个关键“摇摆州”)、参议员以本州为单位的选区以及众议员的更小选区。只有将产业和选区加以结合,才能深入理解美国的贸易决策逻辑。
(一)国际贸易收入的国内分配效应:阶级联盟和行业联盟
“一国经济的国际化(包括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会在一国内产生赢家(winners)和输家(losers),二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国际经济学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贸易收入分配模型,即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以下简称赫—俄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以下简称李—维模型),分别强调贸易收入的要素所有者(阶级)逻辑和贸易收入的行业/产业逻辑。国际贸易收益在国内社会的不同阶级和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均衡分配是不同行为体间贸易政策偏好分化的根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联盟理论正是以国际经济活动带来的阶级分化和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分别提出了阶级联盟和行业联盟这两种影响决策过程的政治行为。
赫—俄模型强调要素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活动的影响,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往往出口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和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进口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相对缺乏和昂贵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贸易会使得本国充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报酬提高,而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报酬降低。所以受益者将支持自由贸易,而受损者将支持贸易保护。罗纳德·罗格夫斯基(Ronald Rogowski) 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将要素界定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研究了不同要素所有者在贸易中的收益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联盟。由于资本、劳动力、土地是传统上划分阶级的标准,故这种联盟被称为阶级联盟。
李—维模型认为,生产要素是固定于某个行业的,当这个行业衰落时它也不能自由流动到另一个上升的行业中去。该模型认为,贸易会使得出口行业的真实收益增加,进口竞争性行业的真实收益减少。由此,贸易会对不同部门/行业的同一要素有着不同影响,要素所有者的政策偏好与所属的行业/部门紧密相连,出口行业将倡导自由贸易,进口竞争行业将支持贸易保护。不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均采用此模型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工具。
另一位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J. Hiscox)尝试对以上两种路径加以融合。融合的关键在于关注行业间要素流动水平,它指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不同行业间转移要素的能力和倾向的程度或水平。他认为不同的要素流动水平决定了贸易收入分配所导致的究竟是阶级联盟还是行业联盟。具体而言,当一国要素流动程度低时,更容易形成狭隘的以行业为划分的联盟;当一国要素流动程度高时,更容易形成广泛的以要素所属阶级为划分的联盟。希斯考克斯采用行业间工资和利润率等作为指标来测量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程度,其背后的原理是如果要素流动性很低,那么行业收益差异就会因为要素流动不畅而加剧,因此较大的行业间工资和利润率差异就意味着较低的要素流动水平。希斯考克斯考察了美国自19世纪至20世纪大部分年间的劳动力工资和各行业回报,发现其要素流动水平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开始有明显下降趋势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他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工业化技术的进步使得劳动技能和技术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它们在拥有不同技术特征的行业之间流动的难度日益加大。
21世纪以来,由于技术飞速进步导致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行业间的要素流动性进一步降低,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往往被固定于某种产业之中,贸易收入的分配效应从要素分化进而转化为行业/产业分化,由此导致社会联盟也主要表现为行业联盟的形式。美国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进一步增强了对劳动力专业化程度的要求,例如半导体、医疗等高科技产业要求掌握专门物理学或生物学知识,而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也要求掌握设备操作或生产工序等特殊技能,这种日益显著的行业门槛降低了要素流动性。在这种背景下,不同要素所有者在国际贸易中究竟是受损还是受益更大程度上由其所属行业的特征所决定,更小程度地由其所拥有要素的特征所决定。换言之,美国的社会分化形式更多地体现为行业联盟而非阶级联盟。
无论是阶级联盟还是低水平要素流动性下的行业联盟,均能充分阐明贸易政策背后的微观社会基础,但它们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未能对“社会联盟”如何影响政策决策提供完整解释。社会联盟理论内部的这两条路径仅仅从理论高度上对秉持竞争性政策偏好的群体和社会联盟进行了分类。但是,考察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分化只是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的第一步,关于第二步即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如何演变为政策结果,社会联盟理论却语焉不详。这是该理论的一个内在缺陷,而这个缺陷源自它对国内制度结构的忽视。正如希斯考克斯所提出的,“下一步应该分析社会分化和制度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形成贸易政治模式的”。
换言之,国内政治制度充当了多元利益诉求与实际政策结果之间的转换器,也就是拥有共同政策偏好的“社会联盟”影响政策制定所凭借的制度渠道。在这个意义上,以阶级分化或行业分化为基础的联盟主要体现为美国各类利益集团,比如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劳联—产联以及代表不同行业利益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农业利益集团、工商业利益集团等,它们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基本和主要方式是游说活动。虽然利益集团游说是美国民主政治的重要部分,但它只能算作一种非正式和非制度化的干政途径。游说所产生的政策结果在很多时候是模糊不清的。因此,社会联盟理论下既有的阶级路径和行业路径未能在社会利益分化和政治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直接有力的联系。
而不同层次的选举是社会联盟影响政策制定所凭借的最为正式和制度化的渠道,竞争性选举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石,是社会群体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渠道,美国决策权力的内层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美国的产业发展往往伴随着某特定产业在某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的现象。那么原本以产业/行业/部门分化为基础的贸易收入分配效应将进一步转化为以地理区域分化为基础的形式,这为考察社会联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路径,即以地理分化为基础的联盟。这种路径实际上是行业联盟路径的一个变种,相较于两种既有路径,地理联盟路径最大的优越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最核心的政治制度即选举制度密切相关。二者都以地理区域划分作为基本原则,从而可以在从政策偏好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中提供更加直接有力的传输链条。
(二)产业集聚与贸易收入分配的地理分化
产业活动在某些地理空间的集聚现象在新经济地理学中被称为产业集聚(industry cluster),具体是指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在一个特定产业领域内或产业链条上的相关企业或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或互补性,在地理上不断集中,进而形成产业集群的现象。产业集聚不仅指代公司或工厂等显性实体的集中,还蕴含着资本、人才、科技等各种隐形资源的地理集中。
产业集聚主要有资源禀赋条件、规模经济效应、区域产业政策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经济生产活动的地理分布受到资源禀赋条件的约束,考虑到资源供应的便利性,最早的产业分布完全是以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地区差异为基础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土壤等条件,自然地形成了不同作物的农业生产分布;工业革命初期,工业生产离不开资源,缺乏燃料和原料犹如“无米之炊”,因此近代工厂主要集中建立在水源或煤铁资源产地附近以及一些交通运输便利的地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对知识、技术、人才等新型资源的依赖逐渐增加,尤其是高端制造产业,因此这类产业往往靠近大学、科研院所分布。第二,产业集聚受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的驱动,大量种类相似的企业在特定地区集聚,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获取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便利,例如劳动力共享、信息传播和技术外溢等,从而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因此,当某些地区由于资源优势等因素而率先发展起某类产业后,其他相关企业在区位选址时就倾向于在规模效应的驱动下向该地区聚集。第三,区域产业政策也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原因,即政府为了实现某种产业布局规划而制定的区域性政策,诸如针对特定产业的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等,以此吸引相关企业向该地区集中,进而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实现更快发展。
在工业化进程中,美国显示出明显的产业集聚特征。随着20世纪以来交通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这种集聚效应更加突出,例如底特律的汽车产业集聚、硅谷(Silicon Valley)的高科技产业集聚、波士顿的生物医药集聚、曼哈顿的金融产业集聚、好莱坞的影视娱乐业集聚等。例如,硅谷是世界著名的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产业区,英特尔、苹 果、谷歌、脸书、雅虎等众多大型高科技公司总部纷纷在此落户,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众多世界一流大学也都分布于此,源源不断地为硅谷输送人才。再如,位于堪萨斯州中南部的威奇塔市(Wichita)是美国主要的飞机制造中枢,有“世界航空之都”的美称,不仅聚集了塞斯纳、比奇、雷神、波音、空客五家飞机制造商 的工厂和麦康奈尔空军基地,而且还拥有雄厚的航空研发资源。比如威奇塔州立大学具有实力强大的航空工程专业,被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为航空研究经费全美第四的高校,同时在来源于企业界的航空研究经费方面被评为全美第一。
美国的产业集聚现象为理解国际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后果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即以地理分化为基础的贸易收入分配效应和相应的以地理区域为单位的社会联盟形式。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产业的地理分布及政策偏好进一步左右着不同地区所持的贸易政策偏好。具体而言,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或出口导向型产业依赖出口获得利润,当该国对外实施贸易保护时,出口导向型产业往往也是他国贸易报复的对象,因此这些产业所集中分布的地区往往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对于国内的进口竞争型产业而言,在开放经济体条件下,他国进口产品会对自身竞争优势造成冲击,从而成为国际贸易中的“输家”,所以这类产业所在的地区一般支持贸易保护、反对自由贸易。
美国2003年9月的舒默议案鲜明地体现了贸易收入在地区间不均的分配效应。舒默议案认为中国低估人民币币值15%—40%,通过“货币操纵”不公平地获得贸易优势,损害了美国制造商的利益,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调整汇率,否则美国应该对所有 进口中国产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在中美贸易往来中,较低的人民币汇率意味着中国厂商得以在不牺牲利润的情况下,在与美国同类商品的竞争中获取低价优势,这将损害美国本土制造厂商的利益,尤其是那些进口竞争型的传统制造业(如钢铁、纺织),事实上这些行业所集中分布的州或选区议员正是舒默议案的推动力量,如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及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唐纳德·曼祖洛(Donald Manzullo)等。另外,对华加征惩罚性关税将招致中国严厉的贸易反制措施,这对美国国内依赖对华贸易的产业而言将是一场灾难,因此国会内部也有反对舒默议案的强大声音,比如来自艾奥瓦州和蒙大拿州的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lassley)和马克斯·鲍克斯(Max Baucus),由于担心贸易保护主义损害本州农业对华出口利益,所以提出了更温和的人民币汇率议案。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关于贸易收入分配的地理分化路径只是理想化的理论模式,现实中的产业集聚现象及其导致的贸易政策偏好的地理分化是复杂交织的。一个州或一个地区的主导产业往往不止一个,甚至持有相反政策偏好的不同产业也可能同时集中于一个地区,这或将导致某特定地区政策立场前后多变或同一州或选区议员分裂投票的情形。
(三)美国选举制度与产业地理政治的生成
如前所述,地理联盟路径弥补了阶级联盟和行业联盟路径在与制度建立联系方面的欠缺,从而为社会联盟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提供了更加直接有力的支持。这里的“制度”指的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主要包括国会选举制度和总统选举制度。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按地理区域划分选举单位,而地理联盟路径是从地理分化角度考察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二者均以地区作为分析单位。不同地区的贸易政策偏好进一步转化为特定选区的经济利益诉求,然后通过美国的选举制度投射到政府决策层。
国会是美国贸易决策机制中的立法部门,国会议员在全国各地由选举产生,其投票立场主要受所在州或选区利益的左右。美国国会是以地理为基础的代议机构,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一方面,以地区为投票单位的代议制保证了美国所有地区的各种利益和诉求都能够在国会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每两年的改选制度意味着议员们需要频繁地应对竞选连任的压力,从而迫使议员不断地考量和落实选民的实质性诉求。国会投票是议员们参与决策的主要途径,选民的利益诉求是决定议员投票行为的首要动力。虽然影响国会投票的因素众多,但“凡是涉及具体的选区利益,国会议员的党派属性、自由或保守的政治立场,对议员的贸易政策倾向和投票行为的影响已经十分微弱”(见表1)。国会议员最为关心的就是重新当选,这决定了他们在国会投票时总是将选区利益置于首位,“议员们对他们的投票记录都很重视,因为他们认为选民将在再次选举时作参考”。守护好自己所在选区的利益是国会议员维持自身政治生命的唯一方式。
总统是除国会以外美国对外贸易决策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总统的行为虽然比国会更不易和更少受到特殊利益的影响,但仍受到选民压力的约束。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制度,选举人团制度和“赢者通吃”规则一方面将总统的选民基础从全国转化为以州为单位,另一方面也使分散的选民利益得以在州层面形成聚合,从而强化了州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及其在总统选举中的显要地位。在普选制度下,总统只需要获得全国范围内的大多数选票,而不论这些选票来自哪个地区,因此所代表的是分散于全国的选民个人的利益。但是在选举人团制度下,总统要致力于赢得每个州内的大多数选票,赢者即赢得该州,计票单位从个人转化为州,分散的个人利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以州为单位聚合形成各州的整体利益,总统竞选宣言和政策实践的参照物实际上是各州政策偏好。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美国政治已经高度极化,两党日益水火不容,美国总统越来越代表其选民“基本盘”的利益诉求,而非致力于成为“全民总统”。近几十年来,美国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选举政治地理,即在总统大选中,支持共和党和支持民主党的州相对稳定并大致势均力敌,决定胜负的是少数几个“摇 摆州”。因此,那些能帮助总统在大选中获胜的关键“摇摆州”的产业利益便成为总统胜选后贸易政策的主要施政方向。
总之,美国的贸易政策决定着各地区间的产业利益分配,民主政体下的选举制度决定了政治候选人要代表选区选民的利益诉求,所以在产业地理基础上形成的选区经济利益反过来也成为塑造贸易政策的关键因素,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构成了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基本内涵,也构成美国贸易政治最重要的微观驱动力。
四、美国的产业地理及其政策偏好
在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发展史上,美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产业结构变迁。从殖民时期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再到两次世界大战的驱动,美国从最初的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再到之后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国际竞争压力增强与产业外迁浪潮,原先分布在美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纺织、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日益衰败,但是位于西海岸和南部地区的航空航天制造、半导体、生物医疗等高技术制造业和金融、信息等服务业快速崛起并保持着全球领先地位。美国产业结构的变迁高度体现出地理集中的特征。
在建国前的殖民地时期,美国经济由农业占主导,在土壤、气候和地理的区域比较优势下,不同殖民地的出口产品各具特点:新英格兰殖民地海岸曲折、良港众多,分布有广大原始森林,捕鱼业、采伐业和造船业发达;中部殖民地是主要产粮区;南部殖民地主要种植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经过整个19世纪的发展,美国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国内南北产业布局开始出现分别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差异。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在19世纪上半叶首先实现工业化,生产从手工作坊转移到工厂,马车、家具、纺织、皮革、造纸等工业开始在东北地区集中。19世纪后半叶,随着制造业的局部扩散,北方形成以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和东北中部地区为主的制造业带。同一时期南方仍然以农业为主,南北产业分化进一步加深。以制造业就业为例,1840年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地区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比例分别为38%和32%,而在其余地区,这一比例只有10%—18%不等。这种产业分布的地理差异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国会内部的关税政策斗争,形成了以南北地区画线的议员投票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世纪50—70年代工业化进一步扩散到美国西部和南部,美国制造业发展如日中天。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在美国爆发,电子、飞机制造、宇航、核工业等新兴工业快速发展。由于资源环境优良和劳动力便宜等优势因素,新的工业部门纷纷布局南部,形成了新工业区“阳光地带”,即位于北纬37度以南、东起大西洋沿岸的北卡罗来纳州、西至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一个地区,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发展尤其迅猛,涌现出旧金山、休斯敦、达拉斯等一批闻名于世的新兴城市以及世界领先的电子和信息产业集聚地。这一时期,农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继续下降,工业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与之相对,服务业在国民收入的占比不断上升,并从50年代超过50%。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重心逐渐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同时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产业结构呈现出高科技化和去工业化的新特点。随着日本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中独占鳌头的地位逐步受到来自日本和德国等竞争对手的挑战。这一时期,尽管美国制造业总体有所衰落,但美国在高端制造和金融服务领域仍然领先世界。随着传统制造业不断外包给新兴经济体,底特律、匹兹堡等传统工业城市逐渐衰败,面临失业人口增加、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但是那些以金融、娱乐、医疗、信息服务等为主导产业的城市,诸如纽约、洛杉矶、亚特兰大等,人口和经济得以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中国通过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美国的产业结构越发“金融化”和“空心化”,传统制造业进一步萎缩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遭受重创。自此,美国开始推出“再工业化”战略,旨在吸引制造业回流和重振美国制造业,但这一战略能否成功还存在诸多变数。
(一)美国的农业地理及政策偏好
从农业生产总值来看,美国农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大平原地区,其次是东南部地区和五大湖地区。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农业产值最高的州,2017年农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近400亿美元,在全美农业总产值中占比高达19.76%,艾奥瓦州、得克萨斯州分别以5.69%和5.50%的占比位居第二和第三,位于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的农业产值也都进入了全美前十。从农业就业来看,农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在全美的分布基本与产值分布一致。从2017年种植业就业岗位数据来看,占全美农业就业岗位比重前五的州分别是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俄亥俄州、艾奥瓦州和华盛顿州。
从具体的作物来看,由于气候、土壤等条件差异,美国农业种植带主要可划分为五大专业区:第一,东北部的乳畜带,包含西弗吉尼亚州以东共计12个州,是以奶牛业为中心的牧草乳酪专业化生产地区,生产的牛奶和奶制品占全国一半以上。第二,中北部的玉米带,包含艾奥瓦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密苏里州五个州,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玉米专业化产区,该区除了种植玉米外,也是美国大豆的专业产区。第三,大平原小麦区,主要包括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五个州,该区小麦的播种面积约占美国的70%。第四,南部的棉花带,美国棉花产量的70%集中在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四州,其中得克萨斯州是美国棉田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州。第五,太平洋沿岸的综合农业区,该区气候类型多样从而适合多种作物生长,西北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小麦产量约占全国小麦产量13%,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则供应着全国51%的水果干果和32%的蔬菜,该区水稻种植也很突出,产量约占全国的18%。
从农业出口来看,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农业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存在贸易顺差的部门,农业出口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2017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高达1405亿美元,占整个货物出口的9.1%。其中,大豆出口历来是美国农业出口创收的最大贡献者,2017年美国大豆出口金额高达216亿美元,远远高于位居第二的玉米(90亿美元)和第三的坚果(85亿美元),其后依次是牛肉(73亿美元)、猪肉(65亿美元)、小麦(61亿美元)、棉花(58亿美元)、乳制品(54亿美元)。另外,从出口占总产量的比重来看,坚果和棉花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最高,如美国核桃总产量的79%和棉花总产量的76%用于出口,其后依次是大米(55%)、大豆(50%)、 小麦(46%)、玉米(21%)、猪肉(21%)、乳制品(15%)和牛肉(10%)。
总而言之,美国是一个世界性农业生产强国,有限的人口使得其农业生产供应超出了国内消费需求,开拓稳定海外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成为农业集中地区的核心政策诉求,因此农业人口往往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尤其是大豆、坚果等出口导向特征明显的农产品行业从业者。由于美国各州不论人口多寡和面积大小均有两名联邦参议员,尽管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产值和人口数量都很低,但因为该地区州的数量多,因此它们在参议院影响力巨大。这成为美国农业在美国政治体系中获得不成比例的优势的重要原因。
(二)美国的制造业地理及其政策偏好
从制造业生产总值来看,美国制造业集中分布在三个带状地区:一是以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为主线的中央东北地带,二是以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为中心的南部地带,三是由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连接起来的太平洋沿岸地带。以上这些州中的大部分在2017年制造业实际GDP排名中都进入全美前十。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在创造制造业就业方面名列前茅,分别占全美制造业总就业的10.7%、7.0%、5.4%和4.8%(见表3)。
从制造业的下属类别来看,美国制造业的分布呈现出鲜明分化的特点,具体体现为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分化。美国制造业集中分布的地带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专门工业区,分别是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五大湖区“铁锈地带”(也指东北部工业区)和以先进制造为主的南部“阳光地带”(包括南部工业区和西部工业区)。首先是工业发展最早的东北部工业区,包含了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纽约州等地区,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是美国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集中分布着全国的钢铁、机械、汽车、化工、纺织等传统工业,著名工业城市有汽车城底特律、钢铁城匹兹堡和克利夫兰。然而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曾经显要的东北工业区沦为“铁锈地带”,一度辉煌的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也陷入困境。其次是过去以农业为主的南部工业区,分布有美国新兴的石油、飞机、宇航、电子等工业基地,主要工业城市为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它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太空城和美国最大宇航中心约翰逊宇航中心的所在地,也是美国的能源和石化工业中心,坐落着美国著名能源公司马拉松石油公司和菲利普斯,此外该地区在生物技术和医疗等行业也处于领先地位。最后是太平洋沿岸的西部工业区,这里电子、计算机、半导体、飞机等高科技工业发达,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拥有美国乃至世界领先的高新技术研发基地,不仅汇集着思科、惠普、苹果等全球领先的信息科技公司,最早研究和生产半导体芯片的英特尔、高通、博通等美国半导体巨头也都分布于此。此外,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还是世界最大飞机制造商波音的总装线所在地。
美国制造业的地理分化特点直接导致了不同地区的贸易政策偏好:一方面,随着钢铁、纺织、家电甚至汽车等产业的不断衰退和外迁,传统制造业沦为美国的夕阳产业,在美国属于进口竞争部门,往往也是美国巨大贸易逆差的来源,因此这些产业一般支持贸易保护;另一方面,美国在飞机、计算机、电子、半导体、生物制药、医疗设备等先进制造业领域仍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这些高端制造产品往往也是美国对外出口的一个重要类别,因此这些产业一般积极寻求扩大国际市场,主要支持自由贸易,但是作为高科技行业它们对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强烈的政策诉求。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高科技制造业在参众两院均实力强劲,尤其是在众议院,拥有比农业更大的影响力。
(三)美国能源地理及其政策偏好
美国的大国经济需要能源产业的驱动,因此能源产业特别是油气开采业对于美国至关重要。从油气开采业的经济产值来看,根据2017年美国油气开采业实际GDP分布,美国油气开采业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地区。得克萨斯州当属美国第一大油气资源开采州,2017年油气开采业实际GDP占全美总值的54.47%,该州由油气开采所创造的就业占全美油气开采总就业的39.68%。此外,西南部地区的其他州如俄克拉荷马州、科罗拉多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斯加州、新墨西哥州2017年矿产开采实际产值分别占到全美总值的10.63%、4.48%、3.44%、3.04%和2.95%,排名都进入全国前十,位于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分别以6.04%和4.78%位列第三和第四,位于最西部太平洋沿岸区的加利福尼亚州则以3.68%位列第六(见表5)。
从油气储量及加工厂的分布来看,美国油气产业的地理分布广泛而不均。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的80%以上集中于四个州,分别是得克萨斯州(24%)、阿拉斯加州(22%)、路易斯安那州(20%)和加利福尼亚州(19%),其他产油州还包括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怀俄明州、堪萨斯州、密西西比州和北达科他州等。美国的炼油厂主要集中于南部墨西哥湾地区的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这一地区的石油炼制加工能力约占美国的一半;美国天然气储量集中在墨西哥湾沿岸盆地、西部大盆地、二叠纪盆地三大盆地内,而美国的天然气加工厂主要分布于墨西哥湾地区和落基山区各州,包括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马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和北达科他州等。
随着页岩革命所推动的美国能源独立计划的成效日益凸显,美国逐渐跃升为一个能源生产大国并且正在寻求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出口。在能源生产方面,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测,由于美国原油、天然气等产量的增加以及国内能源消费的缓慢增长,预计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并将持续到2050年。在能源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后,实施了一系列以重振传统化石能源为核心的能源政策,不仅放松了对油气开发的监管,而且大力推动油气管网建设,旨在扩大近海油气产能和美国能源出口。这使得美国的油气产业开始深度介入美国贸易政治。因此,作为日益重要的出口部门,美国能源部门一般倾向自由贸易立场。不仅如此,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主要依赖进口钢铁,所以这类传统能源行业往往反对美国实施钢铁关税等保护措施。由于能源产业分布的地理集中度比较高且往往是选区内主导产业,所以在参议院的影响力要强于众议院。
(四)美国的金融地理及其政策偏好
从金融业的生产总值来看,美国金融业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大州,而且是少数几个州的关键城市。由于金融业具有高度的人才资源密集型特征,所以集聚效应最为显著。从州的层面来看,2017年纽约州以占全国19.53%的比重居于金融保险业产值榜首,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分别以9.60%、6.40%和5.80%的占比位列其后,此外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的金融保险业产值也都进入全美前十(见表6)。
从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来看,主要有纽约州的纽约、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其中,纽约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和第一金融中心,更是国际排名数一数二的全球金融中心。这一地位得归功于坐落于纽约市曼哈顿区的华尔街,这里集中了众多著名金融机构和大公司的总部,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以及高盛、花旗、摩根大通等超级金融机构,“华尔街”一词已超越本身的地理含义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服务业的象征。芝加哥作为美国第二大金融中心,拥有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全美第二的芝加哥证券交易所,还有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作为美国12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之一的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以及众多外国银行分行和保险公司。旧金山则是美国西部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有“西岸华尔街”之称,是太平洋岸证券交易所、美国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以及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富国银行等30多个国际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是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的美国金融中心。波士顿也是美国顶级金融城市之一,尤其是共同基金和保险业十分发达,著名的富达投资和桑坦德银行的总部及美洲银行的地区总部都位于此地。
在政策偏好方面,金融服务业集中了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精英群体,而且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金融业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系有着高度的利益诉求,总体上看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是经济国际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要支持者。
总之,美国上述四大核心产业呈现截然不同的地理分布,这种产业的地理分布辅之以美国的选举地理,共同构成了美国对外经济决策的主要微观动力机制。而在中美经贸关系中,那些受到利害影响的敏感产业和敏感选区便成为理解中美贸易战的主要“钥匙”。由于中美贸易战主要体现为“关税战”,双方针对来自对方的进口加征关税,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受到直接负面影响的就是那些被中国加征反制关税的对华出口产业,因此那些对华货物出口的产业和选区也构成了塑造中美贸易战进程最重要的产业地理政治。
五、美国对华货物出口的产业地理政治
肇始于2018年7月的中美贸易战主要表现为针对两国货物贸易的“关税战”,美国对华货物出口的行业和地区是主要的利益受损方。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一直是美国增长最迅速的海外市场,对华出口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009—2018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年均增速为6.3%,累计增长73.2%,大大高于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56.9%的平均增幅;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货物出口市场,是美国飞机、大豆、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等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中国市场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
就美国国内对华出口较大的州或产业而言,中国市场意味着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这些州或产业在涉华经贸议题上一般会更加敏感,往往成为反对贸易保护的强大力量,对美国对华经贸决策施加影响。考察美国对华出口的产业地理特征,有助于中国鉴别美国涉华贸易议题中的敏感州和敏感产业,利用其中反对对华加征关税和支持自由贸易的力量,在美国国内最大限度地拓宽中美贸易的地理支持范围。
(一)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中的利益攸关州
一般而言,对中国出口金额较高的州或者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州在对华经贸议题上具备更强的利益攸关性。下文分别从这两个角度考察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中的利益攸关州,并就其对华出口情况和核心议员政策立场做进一步说明。
一方面,从2017年各州对华货物出口金额来看,怀俄明州、夏威夷州和罗得岛州相对来说对华出口较少,大部分州2017年对华货物总出口额处于8亿—30亿美元区间内,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对华出口规模最大,三州总和约占全美对华出口总额的35%。因此,如果中国对美施加进口限制,那么将会对这三个州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以得克萨斯州为例,该州不仅在对华出口规模方面名列前茅,而且也是能源业和半导体产业这两个对华出口敏感产业的主要分布地区。2017年该州对中国货物出口总额高达156亿美元,约占全美对华出口总额的12.22%;其中对华出口规模最大的商品是石油和天然气,金额高达57亿美元,约占美国对华油气出口总额的82.61%。出口中国较多的其他产品还包括基础化学品、树脂及合成纤维、工业机械和半导体及组件(见表9),因此由这些产业尤其是油气行业所代表的利益构成了影响得克萨斯州参众议员投票立场的关键因素。以政治捐资的数据为证,该州俨然成为美国油气行业的首要代言人。从获得政治捐资的行业组成来看,2018年油气行业以3600万美元成为对该州贡献最多的行业;从油气行业捐资对象来看,2018年油气产业提供资助的前20位竞选者中,共有6名来自得克萨斯州,其中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和众议员贝托·奥罗克(Beto O′Rourke)分别以671806美元和546344美元位列第一和第二。
由于出口导向特征明显,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总体上秉持自由贸易的政策立场,在对华经贸问题上反对“关税战”,但他们同时也代表着州内半导体行业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利益诉求,因此往往也赞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指责。以第116届国会为例,得克萨斯州两名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和泰德·克鲁兹——在贸易议题上均代表着本州出口商的利益,历来是自由贸易的强烈支持者。例如,在2003年日本因疯牛病限制美国牛肉进口时,科宁为解除日本制裁做出了重要努力,而且他积极支持美国和新加坡、智利、阿曼、秘鲁等多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等。克鲁兹更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坚定捍卫者。具体到对华经贸议题,两位议员均反对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克鲁兹认为美国征收钢铁等进口关税,只会招致贸易报复从而将代价转移到本州农民和消费者身上;科宁曾在贸易战螺旋升级之际质问“贸易战将如何结束”,认为“总统非常有信心贸易战会有好的结局,但与此同时人们正对于其对经济、就业和消费价格的影响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但是,相较于中国市场,两位议员还是更看重美国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海外市场,而且在政治立场上更多地将中国视作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在与美国贸易时采取不公平措施。科宁尤其态度强硬,倾向于在中国市场改革、中美技术竞争和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上指责中国。例如,他曾在听证会上公开表示,中国正在对美国企业设置不可接受的市场壁垒,通过准入限制和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侵蚀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工业基础。克鲁兹也曾声称,中国通过非关税壁垒阻碍美国向中国出口拖拉机,对美国制造商而言很不公平。
另一方面,从2017年各州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来看,依赖程度较高的州包括华盛顿州、南达科他州、南卡罗来纳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对中国市场出口金额在它们前五大出口市场总额中的占比都超过30%,其中华盛顿州以43%高居榜首。华盛顿州不仅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很高,而且出口规模庞大,是其他依赖中国市场的大多数州对华出口规模的十多倍,因此中美“关税战”的走向对该州经济及就业来说尤其利益攸关。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是该州对华出口的首要产品,2017年华盛顿州对华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出口占据该州对华出口总额的近75%,而该州对华出口 第二大产品机动车辆仅为6.71%,因此航空产业构成了左右该州议员在涉华经贸议题上投票立场的最重要的利益基础。以波音公司2018年政治捐资的数据为例,华盛顿州议员是波音最主要的捐款目标,在其资助的前20名竞选者中,该州参议员玛丽亚·坎特韦尔(Maria Cantwell)获得捐款金额位列第一,该州众议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金·施里尔(Kim Schrier)、迪诺·罗斯(Dino Rossi)也都进入前20名。
华盛顿州的国会议员总体上秉持自由贸易的政策立场,但与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对华强硬态度不同,该州两位参议员在涉华经贸议题上态度较为友好,不仅反对对华加征关税,而且主张改善与华关系。第116届国会中,华盛顿州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帕蒂·默里(Patty Murray)和玛丽亚·坎特韦尔(Maria Cantwell)——均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二人均支持NAFTA和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支持建立或扩展与秘鲁、阿曼、新加坡、智利、安第斯国家的自由贸易,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支持给予越南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支持将普通商品从国家安全出口规则中移除。具体到对华政策立场,两位议员均反对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担心招致贸易报复,尤其担心中国针对航空航天产品等加征高额关税。例如,2018年3月,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301”调查并对中国产品加征新关税后,坎特韦尔随即在一次听证会上抨击美国政府在中国与贸易问题上笨手笨脚,不仅未能增加美国出口,反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她主张通过美中全面对话而非关税战的方式解决贸易分歧。再如,2019年3月,默里和坎特韦尔等共同致信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呼吁他保护美国多晶硅制造业不受中国关税的影响,以挽救华盛顿数百个高薪职位。
对华出口规模及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是影响不同州议员对华贸易态度的重要因素,尽管其效果与议员的党派、意识形态立场、选区亚裔比例等其他因素也有关联。从结果来看,虽然得克萨斯州对华出口规模首屈一指,但中国市场并非其首要海外市场,所以得克萨斯州对华贸易依赖程度不如华盛顿州那样强。相应地,美中贸易摩擦对得克萨斯州而言不如对华盛顿州那样利益攸关,这也是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对华态度强硬而华盛顿州参议员对华态度友好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加强与美国地方的经贸联系时,不仅需要重点关注那些对华经贸敏感的州和选区,同时也应关注它们对华态度的差异及背后的复杂根源。
(二)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中的利益攸关产业
除了从利益攸关州及州内产业布局的角度出发外,还可以从利益攸关产业及其全美布局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美国对华货物出口的产业地理政治。从贸易立场来看,钢铁、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一般寻求政府关税保护,而农业、航空等部分高端制造业、油气等能源行业一般反对关税保护,这类产业在中国具有重要出口利益,往往反对对华加征关税、支持自由贸易,它们的地理分布格局深刻影响着国会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分化及利益联盟。
2017年美国对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为1277亿美元,对华出口货物涵盖各行各业,敏感产业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制造业、农业、能源业等。具体到商品细类,根据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主要商品前五名依次是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油籽和谷物、机动车辆、半导体及组件、石油和天然气。中国是美国飞机、农产品、汽车、集成电路的重要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飞机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17年美国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飞机、20%的汽车、14%的集成电路、17%的棉花都销往中国。
这些产业往往是美国对华货物出口中的利益攸关产业,其地理分布都呈现出集聚特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中分布在中央西北区,大豆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区,半导体芯片等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集中分布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南面的硅谷一带,油气资源集中分布在全国五大油气区30多个油气盆地中。五大油气区分别为墨西哥湾含油气区、北美地台含油气区、加利福尼亚含油气区、落基山含油气区和阿拉斯加含油气区。
第一,运输设备方面,美国对华出口的运输设备主要是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和机动车辆,这两类商品2017年对华出口额分别达到163亿美元和101亿美元,位居第一和第三。从产值来看,机动车辆及零部件类制造集中分布在中央西北区的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等,此外在得克萨斯州也有较多分布,而除机动车辆外的其他类运输设备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等几个大州。美国主要的航空航天制造商包括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波音公司,位于马里兰州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位于堪萨斯州的塞斯纳飞机公司和豪客比奇公司,位于明尼苏达州的西锐飞机设计制造公司等;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则集中分布于有“汽车城”之称的密歇根州,包括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位于密歇根州奥本山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美国的航空和汽车制造部门是贸易战的有力反对者,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贸易反制措施会损害它们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出口利益,另一方面也由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会提高它们从中国进口部分零部件的成本。航空产业方面,波音作为美国最大出口企业,在手订单中约20%—25%来自中国客户,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主张双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为此,波音及其高管不仅频频公开表明立场,还积极开展幕后活动密集接触两国政府,以避免贸易战升级。汽车行业方面,美国汽车制造商联盟(Auto Alliance)公开反对美国对进口汽车进行“232调查”和对华加征关税,并在2018年12月对美中达成贸易休战共识及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表示支持。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主要车企也纷纷发声反对对华加征关税,向特朗普政府施加压力。此外,汽车制造商联盟还联合其他众多美国制造商,在国会内部共同支持修正《贸易扩展法》(Trade Expansion Act)第232条,旨在强化国会在限制总统单方面采取贸易行为上的作用。
第二,农产品方面,2017年美国油籽和谷物对华出口额达到137亿美元,位居第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是食用油籽,其中主要是大豆,2017年全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占其总大豆出口量约一半以上,共计3286万吨,金额为139.45亿美元。因此,大豆是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中的主角。美国大豆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区,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数据,2018年美国各州大豆产量前十名依次是伊利诺伊州、内布拉斯加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艾奥瓦州、密西西比州、西弗吉尼亚州、 纽约州、肯塔基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在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下,美国大豆种植业成为中国反制关税措施的最大受害者。作为该行业的主要利益集团,美国大豆协会(ASA)立刻表达了针对美国对华关税举措的强烈担忧与反对,并联合其他农业利益集团共同游说国会和施压政府。2018年4月12日,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发表证词,强调中国作为美国大豆出口的强劲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实施关税和贸易战对全美豆农的持久负面影响。此外,该协会还在2018年7—8月加入了“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Farmers for Free Trade)”组织,该组织通过电视广告、社交媒体等渠道积极宣传自由贸易,旨在“扩大美国农民的声音,以确保美国决策者了解关税在地方层面造成的痛苦”。加入“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可帮助美国大豆种植者联合其他农业力量,增强对特朗普政府的约束力。
第三,半导体及组件是美国对华出口的第四大产品,2017年出口额为69亿美元。美国半导体产业全球领先,占据一半的全球市场份额。与传统制造业的外移现象不同,将近一半的美国半导体公司将制造基地留在美国,目前在全美19个州内共设有70个半导体制造设施或晶圆厂,其中在俄勒冈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分布最为密集。根据瑞银(UBS)统计,按照营收占比计算,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美国半导体企业包括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思佳讯(Skyworks Solutions)(中国市场营收占比为80%)、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通(Qualcomm)(占比63%)、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威讯联合半导体(Qorvo)(占比60%)、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博通(Broadcom)(占比52%)、位于爱达荷州的美光(Micron)(占比50%)、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得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占比43%)等。
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的关于对华“301调查”的意见书,该行业也对美中贸易战持反对立场。该协会虽然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在不公平贸易举措方面的指责,但不赞同贸易战这一解决方式,原因有两点:一是由于中国是美国半导体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二是由于中国在美国半导体产业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2018年10月,随着贸易战的升级,美国的半导体公司感受到了刺痛,比如VanEck Vectors Semiconductor ETF(SMH)和英特尔的股价就在2018年9月24—25日均下跌2.5%。对此美国半导体企业纷纷警告称,新的关税可能损害其竞争力和利润。
第四,石油和天然气也是美国对华出口的前五大商品之一,2017年出口额为69亿美元,与半导体及组件并列。在油气产量方面,根据EIA数据,2017年美国约65%的原油产自得克萨斯州(38%)、北达科他州(11%)、阿拉斯加州(5%)、加利福尼亚州(5%)和新墨西哥州(5%),约18%的原油产自位于墨西哥湾联邦管辖海域近海的油井。2017年,美国5个州的干燥天然气产量约占美国干燥天然气总产量的65%,分别是得克萨斯州(23%)、宾夕法尼亚州(20%)、俄克拉荷马州(8%)、路易斯安那州(8%)和俄亥俄州(6%),约4%的干燥天然气产自联邦墨西哥湾近海。在油气企业方面,美国最大的油气公司是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2018年市值高达3445.5亿美元。其次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雪弗龙公司(Chevron),2018年市值达2390.6亿美元。其他主要油气公司依次为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依欧格资源公司(EOG Resources)和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等。
能源行业利益集团也是反对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的重要力量。2018年8月9日,美国石油协会(API)主席斯蒂芬·康斯托克(Stephen Comstock)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301条款”委员会前提供证词,强调美国拟议增加“301条款”关税将对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造成负面影响。2018年8月13日该协会致信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再次对政府根据“301条款”对中国产品尤其是钢铁产品征收关税的举措表示反对。原因一方面如协会主席杰克·杰拉德(Jack Gerard)所声称的,“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很多建设项目都依赖外国钢铁(尤其是中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行为不符合美国能源复兴和建设世界级基础设施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则由于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石油公司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贸易反制的靶子。
此外,以上几个产业还连同美国国内其他反对对华贸易战的利益集团结成联合阵线,以最大限度地聚集和扩大针对对华关税的反对声音。包括美国石油协会、服务业联盟、全国零售业联合会等在内的近150个利益团体共同成立了“美国人支持自由贸易(Americans for Free Trade)”联盟。该组织首先大力开展草根活动向基层宣传“关税对美国腹地的损害(Tariffs hurts the heartland)”。其次,通过致信特朗普、莱特希泽以及重要国会委员会及议员,积极游说国会与政府,强调关税及随之而来的贸易报复对选民的伤害。此外,还联合“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组织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起耗资300万美元的运动,向决策层施压,认为“特朗普希望以关税为筹码得到长期贸易协定的做法由于会带来短期经济痛苦而十分不值得”。
总之,美国的航空、汽车、大豆、半导体及能源等产业都对特朗普对华关税战秉持强烈反对立场。不过,美国对华出口特征和美国产业地理格局是动态变化的,随着中美贸易结构和美国产业格局的发展演化,不同州(选区)或产业的利益诉求和政策立场也会随之变化。
六、结论
美国对外贸易决策在国内政治层面受到产业地理因素的影响,在产业地理基础上所形成的选区利益是美国政治决策最重要的微观动力之一。基于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效应,美国国内出口导向型产业的聚集地往往秉持反对关税保护、支持自由贸易的政策立场。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美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航空航天产品及零部件、油籽和谷物、机动车辆、半导体及组件、石油和天然气,它们都集中在特定的州和选区。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中分布在中央西北区,大豆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区,半导体芯片等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业集中分布在硅谷一带,油气资源集中分布在得克萨斯州等中南部地区。以上这些产业基于在中国的出口利益强烈反对特朗普对华关税措施。
对中国而言,可以利用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特征,在美国国内最大限度地拓宽中美贸易的地理支持范围,进而改善中美经贸关系。要重点关注那些对华经贸敏感的州或地区,保持和加强与这些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是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州(比如华盛顿州、南达科他州、南卡罗来纳州、新墨西哥州等)以及对华出口主要产业集中分布的地区(比如主产大豆等农产品的中西部区、油气资源密集分布的得克萨斯州等)。这些州和地区往往支持扩大对华贸易,主张改善美中关系。在必要时可以考虑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针对美国对华出口的敏感州和产业实施贸易报复,比如大豆、汽车、化工品等,通过增加它们的利益损失来调动其反对贸易战的积极性,增加对美博弈筹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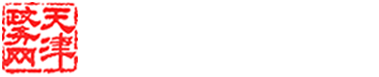



 津公网安备12010102000496号
津公网安备12010102000496号